“遗产酌给制度”下的正义坚守——三十年继父子深情守护终获法律肯定
在继承纠纷案件中,法定继承人往往占据天然优势,但总有一些“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渴望得到法律的认可与公平对待。当委托人M先生从代理律师手中接过判决书时,这位为毫无血缘关系的继父养老送终并守护了三十年的普通人,终于在法律文书上看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认可——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决他获得被继承人L老先生名下遗产1/3的份额。这个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是德禾翰通上海办公室合伙人王琰律师、上海办公室李琳律师用两年时间突破重重法律障碍,最终为委托人争取到远超常规的遗产份额,是我国“遗产酌给制度”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一次突破性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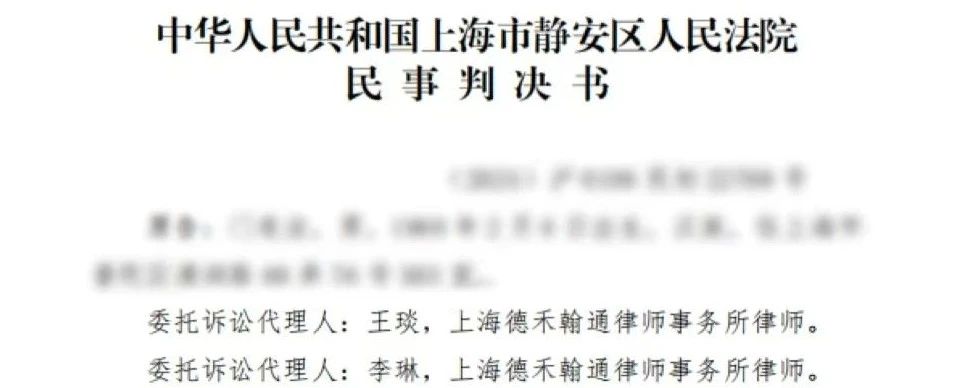
01 案情回顾:三十载照料,非法定继承人的继承诉求
委托人与被继承人L老先生虽无亲生父子的血缘关系,却有着三十年的深厚羁绊。
1980年,11岁的委托人被姨妈S某某“过继”为养子(无收养手续),从老家来到上海与S某某共同生活。S某某原配丈夫去世数年后,S某某与L老先生登记结婚(此时委托人已成年),委托人便与S某某、L老先生共同生活,承担起照料两位老人的责任。S某某因病去世后,L老先生与Z某某高龄再婚,委托人依旧不离不弃,不仅特意在同一小区购房方便照顾,更在L老先生患肝癌期间日夜陪护。2015年,L老先生去世后,委托人为其操办葬礼、购买墓地。委托人照顾L老先生三十年,尽到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赡养义务,使L老先生能够安享晚年。
L老先生留下的主要遗产为一套房屋(下称“系争房屋”),登记在L老先生与Z某某名下(初始登记在L老先生名下,后加名Z某某为共同共有人,房屋最初来源为S某某原配丈夫)。L老先生生前未留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L老先生与已故的原配妻子还有一养女L某(有收养手续),成年后鲜有往来。
2015年L老先生去世后,Z某某仍生活在系争房屋内,直至2023年9月死亡,期间委托人对Z某某也给予了照顾与陪伴。Z某某去世后,Z某某与原配丈夫的三名子女(其中一人已入外籍)、L老先生的养女L某提出继承系争房屋的全部产权,认为系争房屋与委托人完全无关,完全无视委托人三十年的付出。
委托人则认为,四位被告虽分别为L老先生与Z某某的法定继承人,却从未尽过赡养义务,故提起本案诉讼,以期一份公正的法院判决。
02 两年鏖战:程序阻碍与严苛举证下的律师挑战
本案的办理过程漫长且充满挑战。从2023年10月正式启动诉讼程序,直至2025年8月判决正式生效,历时近两年。在这期间,王琰律师与李琳律师面临多重挑战:
•程序障碍重重:
案涉当事人关系复杂,户籍、婚姻、身份等证明材料调取难度大。其中一名被告户籍摘抄显示“赴美探亲”,但公安户籍库中无法查询到该人身份信息及去向,存在被告身份不明确的风险,需想办法寻找下落。
四位被告经合法传唤均无正当理由缺席庭审,试图以“消极对抗”拖延进程。代理律师需反复与法院沟通,确保(涉外)公告送达、缺席审理程序依法推进。
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证据异议等潜在阻碍,代理律师需每一步都精准把握程序节点,避免案件陷入僵局。
•身份认定困境:
委托人与S某某的事实收养关系发生在《收养法》实施前,缺乏登记手续,且年代久远,双方养母子关系的认定存在难度。
S某某与L老先生再婚时,委托人已成年,双方能否认定为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子,无法律明确规定,且实践中争议较大,委托人能否享有法定继承权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举证责任严苛:
因被告缺席,原告需承担严苛的举证责任,且需证明“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这一核心事实。
三十年的日常照料多为口头约定和生活琐事,如何转化为法律认可的“扶养较多”证据?
•法律适用争议:
在遗产酌给制度中,“适当份额”并未设定明确的量化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判决支持比例通常较低,甚至保守判决零份额,如何突破这一常规?
03 专业突破:酌给制度下的比例创新
本案的核心亮点在于对《民法典》(本案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有效的《继承法》第十四条,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精神一致)“酌给制度”的精准适用。该制度规定,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分得适当遗产,但“适当”的比例在司法实践中多为较低,甚至零份额。
代理律师不仅对案件事实进行了可视化梳理(人物关系图、案件时间轴、原被告各方与被继承人的关系及扶养程度对比表),更是深入梳理了三十余年的照料细节,走访30年间居住的两地社区,找到邻居、居委会干部、被继承人同事等近十位证人,收集到原告陪同就医的授权委托书、葬礼操办凭证、共同生活照片、婚礼录像等几十份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清晰呈现原告从日常生活照料到病重陪护、从经济供养到精神慰藉的全方位付出。同时,根据对法律条文的深刻理解,发表了全面的代理意见。节选如下:
一、原告与S某某及被继承人L某某关系的认定
我国《收养法》自1992年4月1日起施行,后又于1998年11月4日进行了修订。S某某以“过继”形式收养原告为养子的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施行前,而当时中国法律对成立合法收养关系的条件和程序并未作出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的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
可见,在1992年4月1日《收养法》施行以前,我国承认事实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对此前已形成的事实收养,继续予以保护。因此,本案收养的效力应考虑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并结合风俗民情及收养事实等因素确定。S某某原系原告亲姨妈,S某某按照习俗以“过继”形式收养原告为养子,该收养事实亦得到家族亲戚、左邻右舍认可;且在实际生活中,S某某对原告在经济、生活等多方面给予了支持,原告对S某某尽到赡养义务,因此,S某某与原告之间的收养关系虽然未办理收养登记等手续但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属于事实收养关系,故,S某某与原告收养关系成立,原告系S某某养子。原告系L某某的继子,原告和L某某共同生活了近三十年,双方关系和睦深厚,原告作为主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扶养人,妥善安排了L某某的生养死葬。
二、原告可分得系争房屋比例的认定
被继承人S某某死亡,其析产后所享有的系争房屋房产份额可作为遗产依法进行法定继承。就本案系争房屋的分割,应根据各当事人对被继承人扶养照顾时间、程度,系争房屋的来源及贡献大小以及当事人的生活需要,予以综合考虑。
《民法典继承编理解与适用》1131条规定“需要考虑多种情况确定酌情分得遗产数量。具体包括:...(2)扶养人的情况。主要是扶养人对被继承人扶养的具体情况,扶养时间长短、扶养方式,以及扶养人与被继承人的亲情关系等。分给扶养人的遗产数额应以其对被继承人所尽扶养义务相一致为原则。如果继承人以外的人,对被继承人扶养时间长,付出多者应多给;对被继承人所尽的扶养义务大于被继承人的子女或其他法定继承人,可以取得遗产中的相当数额甚至可以取得大部分遗产。(3)遗产状况和继承人的情况。不管遗产酌给请求权人是受扶养人还是扶养人,在考虑酌情分得遗产的数量时,都应当考虑遗产状况和继承人的情况,主要是遗产的数量、种类以及继承人的数量、经济状况、是否尽了赡养义务、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关系,还要有利于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
本案中,
1.原告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时间长达三十年,远超一般扶养关系;
2.原告在被继承人病重期间承担了全部陪护责任,甚至以“父子”名义签署医疗文件,体现了被继承人的高度信任;
3.L某某的养女作为法定继承人完全未尽扶养义务,与原告的付出形成鲜明对比。
不管是从30年的时间跨度,还是从照顾被继承人的程度:(1)经济付出;(2)生活扶助:日常生活、看病就医;(3)精神支持:精神帮助与陪伴;(4)丧葬事宜、每年扫墓祭奠等。从各项细节安排到实际操办,都体现出原告对被继承人的尊重与尽心。
三、本案对原告的支持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继父子间30年情同亲生父子的故事也让人心感到温暖与感动
“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遗产继承处理的不仅是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还关系到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风尚。遗产酌给制度以事实扶养为基础赋予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酌情分得遗产的权利,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体现了对非法定继承人因感情亲近而产生之照顾行为的奖励或补偿,具有个案平衡的重要功能。原告三十年如一日地照顾并扶养L某某,妥善安排了其丧葬事宜,让这位老人,生有所养,死有所归,这种扶养体现了人世间无血缘关系人之间真挚感情的美好,应当得到法律的高度肯定,这样才能有效地贯彻落实《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倡导良好的养老风尚,实现情、理、法的有机融合。
最终,法院采纳了王琰律师、李琳律师的代理意见,结合原告对L某某的扶养情况、L某某的生活情况、原告与L某某的关系等因素,酌情判决原告获得1/3遗产份额。
这一比例远超同类案件中酌给制度的通常份额,还打破了公众对“非继承人仅能分得少量遗产”的固有认知,成为酌给制度司法适用的突破性案例。
代理律师办案体会
当代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共同生活方式的改变,推动了非法定扶养义务人或者熟人相互协助扶养的扶养模式的出现,这是对传统家庭内部扶养方式的一种有效补充。今后类似本案复杂的再婚重组家庭组合会越来越多。根据相关统计显示,截至2024年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577.62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7.6%。在此老龄化加剧的社会环境下,对没有血缘的继子女给予继父母的支持和帮助多一些倡导,同时也给继子女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保护,这样能更有助于我们这个深度老龄化社会,朝着“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靠”的目标前行。本案中主审法官所展现出的睿智与担当,令人敬佩与欣慰。
实务中,对被继承人物质供养和精神慰藉,是影响判定酌给比例的核心标准之一。本案前后时间长达三十年,且多位被告因无正当理由缺席庭审,对法官查明事实、对原告的举证都提出了严苛要求。在本所律师向法庭提交的大量证据中,很多证据其实都藏在生活的细节中,容易被当事人忽视,比如:一封证明实际生活住址的信、住院文件签字栏的双方身份说明、学生证或工作证上的家庭住址、一张家庭合影、一张缴费单及日常对被继承人的称呼证明等,这就需要代理律师用自身的专业素养不厌其烦地与当事人一遍遍沟通、一点点甄别,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份看似无关的证据。
在继承纠纷中,法定继承并非唯一准则,“权利与义务对等”才是法律的应有之义。只要付出真实存在,专业的法律力量便能让每一份善意都得到尊重,让每一份坚守都收获正义。遗产继承不仅仅是财产分割,更是对善良风俗的确认。委托人获得的不仅仅是房产份额,更是对三十年人间真情的法律背书。在这个老龄化加剧的时代,这份判决恰似一盏明灯,照亮了“老有所养”的法治路径,同时也为律师在后续办案中带来了新的启发和参考。















